论儒,这是个大课题,我所学寥寥,故就只妄论一下洪玄机的儒到底差在哪里。
洪玄机的儒,很多人都明白,是朱程理学。
朱程的理学何以现在诟病众多,最主要一点,他的根本思想“去人欲,存天理”错了。很多人也许知道他错了,但不知道这句话究竟错在哪里。
要说理学,必然要先简单说下孟子性善学,“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这里孟子其实省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也正是因为朱程都没有意识到孟子省略的那个重要前提,所以孟子的学说并无大的过错,但到了朱程之时,却成了悲剧。到底是哪个重要前提呢?就是一个”我“。我为何会爱其亲?是因为和哥哥以及其他外人比较,我和我的父母更亲近。我为何会敬其兄?是因为和外人相比,显然我和我哥哥的关系更好。而更外层,显然就是我的朋友,然后则是和我同乡的人,再外圈则是本国的人。所以孟子才会说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想以及推人,由最里层,层层推进,层层实行仁爱。这是其一。
其二,也正因为朱程忽视了我,所以他理解不了了孟子的另一句话,”今人乍见孺子将入於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他们理解了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却把恻隐之心的前提怵惕给无视了。怵惕做何解?恐惧,惊惧的意思。孟子那句话,原意是说看见小孩被扔到水井里,我一下子就感到恐惧,然后生出同情之心。看吧,孟子先生出的是恐惧的心理。他把自己代入了那个小孩,想到那个情景就感到恐惧,然后由己推人,才同情起了那个小孩。可见恐惧之心是恻隐之心的前提。而正是因为朱程理学忽视了我,所以理解不了怵惕,由于理解不了怵惕,他自然要找到恻隐之心是从何而来的咯。于是,他找啊找,看到孟子说人性本善,就认为恻隐之心是天性,是天理。而宋儒,也确实是好学之人,仅仅发现天理,那如何能成圣啊?结果又从礼记中找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好了去欲论出来了。研究至此,宋儒认为还有个问题啊,那就是怵惕到底做何解。有时,你也不得不佩服那些宋儒,他们意识到了物欲是为我,而怕死之心,也是为我,于是乎,中国千年来的悲剧至此产生了!
好了,至此我们理解了朱程理学是如何把怵惕归为人欲的,现在再说说”去人欲,存天理“会如何造成悲剧。宋儒既然认为怵惕是人欲,那么就要练习如何去除恐惧。而”去人欲,存天理“其实也演变成了”去恐惧,存恻隐“。程子门下的高足,谢上蔡就天天在高石阶上跑来跑去,以为我不怕死,人欲去尽,剩下的,自然是满腔的天理咯。但结果却是在另一个宋儒身上显现了,有个叫吕原明的,乘轿渡河坠水,跟从都死光了,他安然坐在轿中,漠然不动!试想,一个去了恐惧的心,如何生出恻隐之心?!既然生不出恻隐之心,那就必然流于残忍,所以程颐说出”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魏东原说,宋儒以理杀人!
联系到阳神中的洪玄机,他是理学大家,自然信奉的也是”去人欲,存天理“所以,我们看到的,永远是那个不动声色的掌握诸天众神的神王洪玄机。他作为人仙,大乾太师,有谁能威胁到他的生命呢?所以,他忘了恐惧,既然忘了恐惧,所以也没了恻隐之心,所以即使他子女死去了,他也能无动于衷。一个能漠视自己子女生死的人,你能指望他会对自己妻子的生死关心么?你能指望他会对天下众多百姓的生死关心么?所以,梦冰云死了,只有洪易这个儿子伤心流泪,所以洪熙洪康以及赵家,贪赃枉法,压迫百姓,他也能漠然处之。试问,如此一个绝情绝义之人,如何能成为”子“?他终究只能做到外表气质上某种相似,而得不到上古诸子的道心,勘不破那圣道。
ps:所出言论,多出自于李宗吾的”恐惧与怜悯孟子,荀子的人性观“以及”天理与私欲论宋儒对人性的扭曲“
by私奔干不干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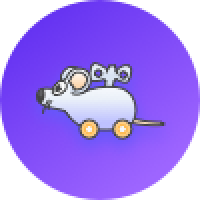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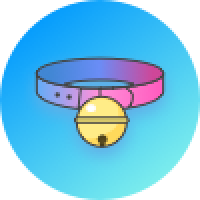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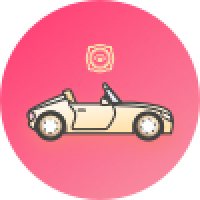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