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浪望着山坡上好像芝麻一般跑得乱七八糟的草木,对玦儿笑道:“老婆,你说若是现在有一群羊,忽然看见自己的饭满山乱跑,它们是会追着去吃草呢,还是吓得转头就跑?”
玦儿嘻嘻笑着道:“若是一群羊我便不知道会怎样,但我知道要是我去山上放把火的话,羊和草都得跑!”
孟浪吃惊地望着玦儿道:“老婆,你什么时候变得像张飞一样了,动不动就要去人家屋子后面放火!”
玦儿很是认真地歪着头想了想,有些不解地道:“为什么说我像张飞呢,玦儿即便是放火也不会像他一般放,否则岂非辱没了祝融一族的名声!”
孟浪眯着眼盯着玦儿,有些怀疑地道:“哦,放火难道还放得出花样来么,难不成能像放焰火一样好看吗?!”
玦儿颇为自豪地一抬头,从怀中取出祝融锥来,那假木王一眼瞥到玦儿手中的祝融锥,脸色募地大变,惊声问道:“你,你是火神后人?!”
“咦,认识老婆的人好像还不少!”孟浪奇怪地看了看假木王道,“我老婆的名字叫做祝融玦,你说她是不是火神后人呢?”
那假木王盯着玦儿看了很久,终于一摆手,山坡上的草木立刻归于沉静,假木王凄然道:“既然这是主人的意思,我无话可说,只求玦儿姑娘手下留情,放过这满山草木,罪只在我一人!”
“主人?”孟浪和玦儿都是一阵迷茫,“什么主人的意思?”
那假木王朝山坡上望了一眼,突然转身扑向玦儿,这一下毫无征兆,就连孟浪都被弄得措手不及,玦儿尚未回过神来,那假木王竟以冲到面前,玦儿下意识地将手中的祝融锥往前一挡,谁知那假木王竟不避不让,径直向祝融锥撞了上来,整支祝融锥自假木王胸中直穿而过,假木王的身体立时燃起熊熊火焰,凄厉的叫声让站在孟浪和莫日根身后的兄弟及元军士兵们不寒而栗。
片刻之后,假木王竟已被烧为一堆灰烬,莫日根若有所思地看着地面,缓缓地道:“他似乎是有意寻死,我总觉得他身上有一个什么秘密!”
“是了,”孟浪也附和道,“他一见到玦儿手上的祝融锥就脸色大变,还说什么是主人的意思,妈的,偏又不把话说完才死,这下子便是把脑袋想破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
玦儿有些不安地皱眉道:“这人好像认识我一样,但我自从离开般若塔之后,一直都和父亲在一起,后来遇上了你们便都没有再离开过,我并不记得见过这样的一个人啊!”
“妈的,说不定这小子便是故意留下个死结,让咱们想得头痛不已,那自然是吃不好睡不好,东瀛王八蛋只要一冲过来便可以把一帮憔悴得树叶一般的傻蛋给灭了!”孟浪释然一笑,呵呵地道。
众人都不禁莞尔,莫日根也道:“现在想这些的确不是时候,若木王和他的大军不在这里,那另外两路人马便万分危急了!”
孟浪这才想起莫日根还不知道兀台大营已被攻破,便将此事以及自己请段和赶赴兀台大营的事告诉了莫日根,莫日根听完一直沉默不语,半晌之后才对孟浪道:“若你是三军统帅,知道大营被攻破,你会怎样?”
孟浪很是为难地挠了挠脑袋,苦笑道:“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做不了这带兵打仗的事情,上次去云南,若不是有老头子和花诗在,只怕我半路上便去见了祖宗了!不过,我想派兵赶去救援总不会有错吧!”
莫日根不置可否地淡淡一笑,回首大声道:“把那个东瀛军的传令兵带过来。”几个游骑手迅速策马而去,不过片刻便将那兀自没有缓过神来的令旗兵带了过来。
过了好半天,那令旗兵似乎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然成了俘虏,立时叽里咕噜叫了起来,孟浪皱了皱眉,低声道:“妈的,若是花诗在肯定知道这小子是不是在拿东瀛话骂老子!”玦儿眼神一黯,假装没有听到。
竖眼睛却走上来对孟浪道:“孟少侠,他在说,即便他被你们捉住了他也决不会投降。”
“哦,你懂东瀛话么?!”孟浪很是讶异地看着竖眼睛道,“你问他,木王究竟在什么地方?”
竖眼睛无奈地一笑道:“就连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木王的替身,这话恐怕也不必再问了。”
玦儿忽然对竖眼睛道:“你告诉他,他现在可以走了,我们决定放了他!”孟浪一阵诧异,莫日根则是对玦儿投来奇怪的一瞥,但两人却都没有表示反对,竖眼睛把这话告诉了那令旗兵,那令旗兵简直听得瞠目结舌,一脸的不相信。
玦儿却也不理会还在发呆的令旗兵,转身对莫日根道:“莫日根将军,既然如此,我们留在这里也没有任何意义,不如赶快到中路援助杨勇他们!”
莫日根微一沉吟,还是下令全军赶赴中路,孟浪虽是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带着兄弟们与莫日根一道起行,那令旗兵一直到完全看不到这数万大军的身影这才相信自己的的确确是被释放了,立刻转身飞奔而去。
莫日根一边走一边看了看玦儿道:“玦儿姑娘,你也觉得那传令兵可疑么?”
玦儿笑了笑道:“若一枝大军之中只有他一人不是草木,你觉得他可不可疑呢?”
莫日根叫过一名万户,命他让大军原地待命,然后对玦儿道:“若玦儿姑娘所料不错的话,那个传令兵现在应该已经上路了,我们若去得晚了恐怕有变!”
玦儿与莫日根、孟浪连同横鼻子和竖眼睛五人重新回到刚才对阵的山坡,那令旗兵自然已经不见,就在这时,三名游骑手自山坡后奔过来,对莫日根道:“莫日根将军,那传令兵越过山坡而去了。”
莫日根点了点头,五个人快速朝游骑手指的方向行去,除了玦儿和莫日根而外,孟浪与横鼻子和竖眼睛心中都是莫名其妙,不知道两人究竟要做什么。
五人赶了一程,募地听到前面不远的一丛树后有说话的声音,便悄悄靠了过去,发现刚才放走的那个令旗兵正与一个背向他的黑炮人说着什么。
竖眼睛低声对大家道:“那传令兵正将刚才的事情告诉那个黑袍人。”
“哦,”那黑袍人竟以非常地道的汉话说道,“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活着呢?!”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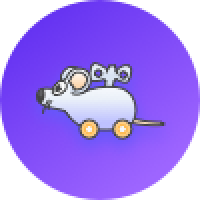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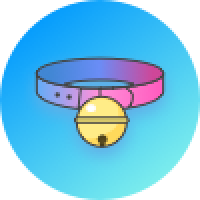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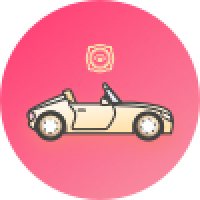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