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溪雨独自蜷缩在角落,看着窗外拍着翅膀的鸟儿。
她宁愿做一只为生存奔波的鸟儿,也不愿意做个任人凌辱的女人。
更可笑的是,她被人强暴两次,都是养父干的。
牧浦云。
或许,传言说的对,他不是人,他是狼。
没有人性,没有情感的狼。
记得十岁时,她害怕一个人睡觉,会搂着他肩膀上哭泣。
“这个世界没有事情是可怕的,是你不敢去正视。”
犹记得那清淡的声音,如同春风一般,缓缓散开,满是温柔。
他轻轻拍着她的背,一下一下,直到她不再害怕。
是的,我不能害怕。
“我要反抗”
牧溪雨突然蹦出这个想法。
她要为自己的自由,为自己爱的权利而抗争。
突然想到,或许,她可以趁牧浦云不注意,在他背后用刀狠狠地刺向他。
就像电视上演得一样,血会染红他的白衬衫,然后他转身指着她。
瞪着一双难以置信,死不瞑目的眼在她面前倒下去。
为了自己的自由,唯有这样。
第二天。
牧浦云回来了。
她趴在窗边向外看。
只见有个秃头的男人大摇大摆走进来,身后带着二三十个又高又壮的男人。
他们吵吵闹闹地踩着草坪走进薄情堡。
牧浦云坐在泳池旁的圆桌边纹丝不动地喝着红酒。
光头男人在牧浦云对面坐下来。
“牧哥,好久不见!”
“你要是不介意可以叫我牧先生。”
牧浦云漠然笑笑:“你也知道我好多年前就不在道上混了,不习惯别人这么叫我。”
“你少跟我摆架子。”
光头男人本就很大的眼睛瞪得都要掉出来。
“阿豹是我兄弟,你最好给我个交代。”
“我最近记性不太好,想不起来谁是阿豹。”
光头男人一把抓起他手边的酒瓶,在桌上砸碎。
用尖锐的断口抵着牧浦云的喉咙:“少跟我装模作样,你以为这还是六年前?
我给你面子叫你一句牧哥,别以为我是真怕你。”
牧浦云瞄了一眼酒瓶,无所谓地将身子靠在椅子上。
“你不用给我面子。”
“我知道阿豹的货让你吞了,还通知□□抓他!”
光头男人缓了口气,又将酒瓶顶到他的胸前。
阴狠地道:“告诉你,只要你把货吐出来,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否则”
他的“否则”还没说清楚,牧浦云突然抓住他的手臂,脚下一扫,顺势手一用力将酒瓶送进那人的胸膛。
一切,发生的太突兀。
等跟进来的那一群人反应过来伸手向衣服里摸的时候,牧浦云已经拖着哀号的光头男人挡住身前,指指他们的身后。
那些人一见自己身后站着许多拿枪的黑衣人,一动不动地僵在原地。
牧浦云抬脚将光头踹得摔了二米远,拿了个纸巾擦擦手上的血。
不疾不徐对身边一个保镖说:“通知□□有人私带枪械,擅闯民宅,可能
意图杀人吧!”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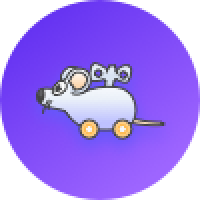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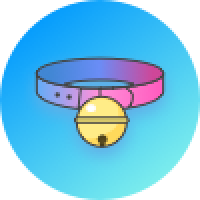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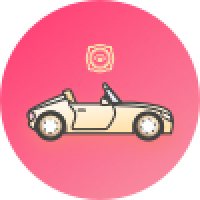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