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润的唇凑了上来,碾转吮|吸,驱散了心头的厌恶和排斥。
受伤的舌被反复tian弄,直到伤口处酥麻一片,浅淡的血腥味完全消失不见,他才微喘着离开。
我睁开眼睛,与他对视。
墨黑色的眸子里,对我的渴求显而易见。
我惧怕,也莫名期待。
如果是尘飞扬,我万万不会推拒,两个人相爱,是必定要走到这一步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我不会因为自己的过去,自私的将自己保护的滴水不漏,去伤他的心。
像是眼神的交锋对峙,谁也不肯先示弱。
过了约莫半刻钟,他深深吸了口气,又缓缓吐了出来。
他一头窝进我的颈窝,双臂缠上我的腰身,闷闷的声音从很近的地方传来,混着彼此震荡的心跳:
“景,我忍不住了。”
我脸颊止不住的发烫,将脸埋在他的肩头,汲取着他身上的气息沉默着默认。
揽在腰身处的手腾出了一只来,解着我的衣衫。
二哥这么做的时候,我只有惊慌,排拒,不知所措和佯装出的淡定从容。
可尘飞扬这么做,心里只有期待和紧张。
他似乎没解过别人的衣带,动作很是笨拙,最后索性直起身子,两只手齐上阵。
上身的衣物除尽之后,他拉过旁边的薄被盖在我的身上。
我:“?”
然后,将混在衣服堆里的素纱禅衣拎起来,走到桌子旁,用跳跃的烛火点燃了薄如蝉翼的禅衣。
世上仅有几件的素纱禅衣,就这么在他手中,灰飞烟灭。
屋子里涤荡着烧焦的味道,青烟弥漫中,我看到尘飞扬转过身,似笑非笑,嘴角微小的弧度是我从未见过的,飘渺邪魅。
他开口,声音依然是刚才那种带着沙哑的低沉:“景,你只怨我什么都不肯告诉你,殊不知,我也怨你。”
“我是个除了亲近之人,绝对不会碰别人,也不会让别人来碰的人,而我想要亲近的人,也不会容忍别人来觊觎和碰触。”
“所以你能想像得到,当我看到你躺在那儿,被人肆意抚触的时候,我会有多生气,多愤怒了吧。”
我垂下眼睑,有些承受不住这样的注视。
他走过来,站在我面前挡住了明亮的烛光,眼前一下子暗了下来,被笼罩在他的身影之中。
他抬手将我沾在脸侧的发丝理顺,阴暗里看不清他现在的表情又是如何。
“我的确很想得到你,可即便你不拒绝,我也绝不会在你会伤上加伤的情况下对你做这种事。”
声音里蕴含着一股子刻意压制着什么的意味。
一阵冷风透过窗户缝袭来,烛影摇动,恍然间如在梦中,蝉鸣虫叫也陡然间消寂无踪,眼里心里耳里只有他一人。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找回我的神智。
这就是被人爱的同时,也爱着人的滋味么?
有他在身边,已经胜过一切,那些仇恨,那些经年不愈的伤口,那些耻辱,那些伤痛,一并变得遥不可及。
不行!
殷溪景,别忘了你是怎么死的,别忘了重生的目的,别忘了那些人是如何将你陷入无间地狱永无休止的折磨!
难道,你还想再来一次那样的结局吗!!!
我幡然醒悟过来,若有似无的旖旎顿时烟消云散,苦苦一笑,将在脸侧徘徊不去的大手抓下,写道:别对我这么好。
想了想,又划拉道:有时间我带你去青楼。
尘飞扬狠瞪我一眼,反手握住我手的力道大的吓人。
不知药效到底能持续多久,第二天睁开眼睛时还是浑身无力。
尘飞扬抱着我去洗漱,早膳过后又伺候着我洗澡,小宝只能在一旁干瞪眼,插不上手,见他神色间透着疲惫,我便让他先去休息。
偌大的浴池里,只有水声作响,我站不稳,被他紧紧搂住腰身贴在怀里,布巾蘸着水,轻柔仔细的洗刷着身体的每一处。
擦到背部的时候,他道:“背上的伤已经好了,只留下很浅的疤痕。”
我点点头,没告诉他偶尔胸腔里痛的厉害,许是留下的后遗症。
“手心里的伤口还没有愈合,不知你还痛不痛?”
我摇摇头,这里是真的不痛了。
无力打掉故意在胸口处滑动的手,我靠在他身上,想起初识时一起洗澡的情景,恍若就发生在昨天。
岁月流逝的太快,我只能死死坚守自己复仇夺皇位的信念能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改变。
尘飞扬是这次命轮的变数,也是能左右我的不安分因素所在。
所以,我只能,尽力的活的像刚重生时的那个我。
快乐,幸福,平和,安居乐业,这些,都不会属于我。
火热发烫的身体将我从不断膨胀的野心里拉了回来。
尘飞扬不知何时气息紊乱,急切的吻从耳后开始蔓延,如星星之火,就要燎原。
他把我的手放到那处硬热,引着我动作。
“坏蛋。”我大着舌头轻笑,努力掩饰着自己的羞赧。
他亲了亲我的嘴角,宠溺味道十足道:“只对你坏。”
夜幕降临时,全身无力的状况才慢慢摆脱,我站在屋子里活动着四肢,望着窗外青灰色的天空,脑袋放空。
忽然脚下一滑,不知踩到了什么,一个趔趄差点往后栽去。
我急忙扶住窗台稳住身子,屋子里还没点亮烛火,尘飞扬在外面乘凉,小宝守在门外,我四下环顾了一圈,确定没人偷袭我后才低头。
一张白纸出现在脚边,我捡起来,上面还留着我灰色的脚印。
我坐到桌子旁,点燃蜡烛,展开纸张看了起来。
这貌似是一封信,但是,没有署名。
没有墨香,证明这信不是最近才写的,那么,是写给谁的呢?
看完纸上的所有内容,我摸着下巴思索了起来。
我身边有位他国国君?毕竟这信里的意思是皇上久未归国,而大殷国的皇帝还在皇宫里呆的好好的呢。
或者,我身边有人认识他国国君,写信让国君赶快回国,那么这个写信的人和他国国君是什么关系?
难道说我身边有细作?
把身边的人挨个过滤了一下,几乎每个都没有嫌疑。
字里行间透着亲昵,字迹清秀,根本不像是出自男人之手。
府里的女人,除了丫鬟,只有柳如是一个。
可她从未踏进我的房间一步,这信又是如何出现在我房间里的?
想不通,干脆不去想,我把信重新折好,将脚印抹掉,放回捡到它的位置。
心里有个猜想,可太过荒唐,于是强自将它压了下去。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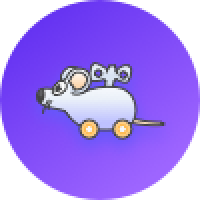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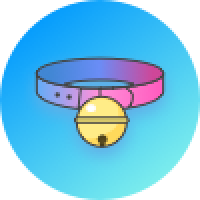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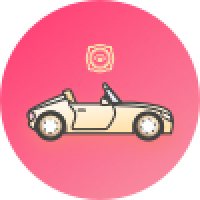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