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刻就把刚才要说的话给忘了,眼睛跟着颜非的手指看了过去。
只见洞口旁用黑色的记号笔画着些弯弯曲曲的古怪线条,有长有短,还有的纠缠在一起。整幅图案足足占了两本杂志大小的位置,在昏暗的光线里却并不显眼。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越看越乱。”我拿手在上面摸了两下,“怎么还是湿的?你就一直在看这个?”
颜非再次盯了它好一会儿,说:“这幅画在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可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非要用这么隐晦的方式。”我愣了一下,就听颜非又说:“我们一定认识他,他怕我们认出他的笔迹,因为他不想让我们知道他曾经来过这里。”
“曾经?”我极其敏锐地扑捉到一个关键性词语,“你的意思是说,他已经出去了?”颜非沉思着点了点头,说:“应该是这样。”
我一下就高兴起来,说:“那你说说这画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线路图?”颜非用无奈的眼神瞥了我一眼,没有吱声。
我的心立刻变凉了,心想这里明明就是个死胡同,我说的确实是废话。我于是“切”了一声,说:“这也能算画吗?你看这一块画的,分明是一团牛屎。”
颜非再次瞥了我一眼,把背包解下来递给我,说:“你要是累了,就靠在包上睡一会儿。我再看看周围还有没有别的记号。”
我明知道颜非是真的在关心我,偏偏心里还是觉得他在烦我,忍不住皱了皱眉。
但等颜非看过来,我就堆了一个笑脸,说:“那你呢,你不困?用不用休息一下?”虽然对自己这种神奇的变脸速度也有点鄙视。
颜非只是瞥了我两眼,然后又继续盯着那幅图案瞧,像是要在上面瞧出朵花来。边说:“我没事,平时忙起来也经常熬夜。”我愣了一会儿,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半晌,我才说:“颜非,将来哪个女人当了你的老婆可真是挺享福的,温柔体贴,还可以当免费保镖。”
这次换颜非愣了一下,但立刻又笑了,说:“要不你给我当老婆算了,免得浪费资源。现在像我这样的好男人可不好找。”脸上的表情怪怪的,看得我突然有点心慌。
我说:“美得你!”然后把颜非的背包放在墙边,坐下来靠在上面,心想他是不是被曾毅晖给传染了,居然也会****小姑娘了。
颜非则笑了几声,什么也没说,只开始在周围石壁上继续寻找记号。也不知道是什么想法,我突然感觉有点失落。
我在旁边看了他一会儿,慢慢地就觉得眼皮子重得不行。才把两只眼睛闭上,突然想起什么,就喊:“颜非。”
颜非立刻应了一声,问:“又怎么了?”
我闭着眼睛伸出手往左边指了一下,说:“那边,饼干和水我都给你留了一半。你的肚子叫唤的声音实在太大了,吵得我睡不着。”
但说完半晌,却没有听见颜非吭声,也没感觉他动。我诧异地睁开眼睛,就发现他正一脸严肃地盯着我。
我愣了一下,以为他突然中了邪,心里立刻就有些毛毛的,急忙伸出一只手在他眼前猛晃了一阵。
就听见他突然严肃地说:“阿舒,谢谢你。”
这次换我笑了。我说:“啰嗦。”
我本来以为在这种气氛里是绝对睡不着的,可没想到一闭上眼睛脑袋就开始昏昏沉沉,不知不觉中就彻底地睡死了。
这一觉也不知睡了多久,等我醒过来时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就看见颜非已经到了石室另一边,还在石壁上仔细地寻找,但看样子并没有什么发现。我立马就对他的耐心佩服得五体投地。
周围的烛光暗暗的,凭蜡烛的长短来看,我应该只睡了一小会儿。于是我挪了一下身子,打算换个更舒服的姿势接着睡。
可就在我刚要睡着时,一根凉冰冰滑腻腻,大概有手臂粗细的东西就贴着我的腰部滑了过去。
我正迷迷糊糊,以为是颜非要在包里找什么东西,就往旁边让了一下。结果那根凉冰冰滑腻腻的东西还是没走,而且感觉很长,起码比人的胳膊要长,像一条长绳子。
我浑身激灵一下,马上清醒了,急忙把两只眼睛睁开。下一个瞬间,就听见从我的喉咙里溢出一声比踩到蟑螂时还要震耳欲聋的尖叫:“蛇啊,救命!”整个人像被火烧了屁股一样又蹦又跳地爬起来就往颜非那边跑。
颜非正对着石壁发呆,被我的惨叫声吓了一跳,转头时脸色一下就变了,大声喝道:“别动!”
我的两只眼睛不住往后瞟,就看见那条蛇正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身子足足有我胳膊那么粗,此时正抬着头直吐信子,一副要扑过来和我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势。
我瞪了颜非一眼,心说,不跑才是傻子,等着蛇来咬我吗?我的脚下没有一丝一毫的停顿。
事实上,事情远没有我叙述的这么慢。就在颜非大喊了一声“别动”之后,他就已经迅速地冲了过来。所以没有等到那条蛇真正扑过来,甚至没等到我有所反应,我就亲眼目睹了颜非一手捏住蛇头并将其拧断的全过程。
这几乎是一瞬间是事情,等到蛇血飞溅出来时,我已经完全瘫倒在地上没法动了。
说实话,这么几个月下来就算再诡异的情况我都挺过来了,可偏偏被这么一条不算很大的蛇给吓个半死。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叫做“怕什么来什么”,说的就是我此刻的状况。
记得周德东先生曾在他的书中这样说: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最怕的东西,每个人最怕的东西都是自己想出来的,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准确地描述出来,那将是一部最恐怖的书。
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很多人害怕的都是原本虚无的东西,也许是怕鬼,也许是怕死,也许是怕孤独。但我却更害怕那些真实存在的事物,以及我们对这些真实存在的事物所不了解的那一面。
比如这条蛇。也许它本身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它和我们人类一样只是某种生物。但请仔细想一想,它是怎样出现的?它为什么会在这时候出现?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有思想吗,又在想什么,为什么攻击我?难道是有人指使它前来?这样无限地想下去,总有哪一点能够触及到我们内心恐惧的极限。
颜非看我半天没动就知道我是动不了了,赶紧过来把我扶了起来。他本来不知道我怕蛇,不过估计这次之后他也就知道了。
“这周围的石壁上什么都没有,估计那个人只留下了那一幅图案。”颜非朝四周看了一下,说,“这回真像你所说的,我们是走进死胡同了,除非再从那条通道出去。”可是,我们敢吗?我分明从颜非眼里看出了这句话。
是啊,我们敢吗?天知道从那里出去又会掉入怎样更加恐怖的循环。正沮丧时,就听见颜非突然“嗯”了一声,像是发现了什么东西。我朝他看过去,就看见他正盯着那条死蛇出神。
我忍不住皱了一下眉,极其厌恶地把视线从死蛇身上移开。心想,不过一条死蛇而已,难道你还能从那上面看出朵花来?
花是确实没有,就听见颜非突然问:“阿舒,你看这条蛇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我浑身一震,视线立刻移回死蛇那边。只见地上一条曲曲折折的爬行痕迹,尽头竟是石室另一边的供桌下面。我和颜非很有默契地对视一眼,朝供桌走了过去。
那张供桌占了很大一块空间,上面却只摆放了一个小香炉,还落了厚厚的一层灰。我们弯下腰去看,果然发现供桌底下有一个宽大的洞穴,足以容得下一个人爬进去。我和颜非再次对视一眼,想的都是:难道那个人就是从这里出去的?
但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一个洞?洞穴里面有多深,通向什么地方?我忍不住皱了皱眉,这个洞究竟是那个留下记号的人挖出来的,还是……可惜还没等我想出什么明堂,一大股腥臭难闻的气味就从洞里直直地散发出来。
我急忙捂住鼻子,还是被那股腥气冲得使劲往后缩了一下。与此同时,就听见洞里再次传出一阵奇怪的响动,就像……就像一个破烂的麻袋被拖在地上走时发出的“嚓嚓”声。
我愣了一下,心想难道是那个留下记号的人又回来了,并且打算在这里常住所以搬来了东西?转过头,就看见颜非也正捂着鼻子一脸沉思状,当然他想的通常来说都比我要靠谱一些。
只片刻的沉思过后,就看见颜非突然脸色大变,急急忙忙地一把拽住我就往后拖。
我被他拽得往后一晃,差点儿闪了腰。急忙从地上连滚带爬地翻起来,只顾闷头闷脑地就往后跑,几步过后一回头,就看见一颗硕大无比的蛇头突然从供桌底下冒出,直直地就朝着我们冲了过来。
这条蛇的身子足有普通油漆桶那么粗,满身都是粗糙坚硬的鳞片,浑身黑不溜秋的颜色,长得几乎看不见尾巴。
等我反应过来,就看见那颗硕大无比的蛇头已经触到我面前,长长的蛇信像水管子般粗细,几乎舔到了我脸上。
我叫了一声“妈呀”,说:“颜非,这……这是龙吧?”然后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颜非根本没搭理我的胡说,无比镇定地拉着我往旁边一闪。只见他的右手看似很随意地一扬,供桌上的一根蜡烛已经旋转着冲着那只巨大的蛇头飞了过去。蛇怕火吗?应该是吧。
谁知那条巨蛇居然不闪不避,长长的蛇信子“嗖”地一吐,“噗”的一声轻响过后,带起的风立刻将蜡烛上那点摇摇晃晃的小火苗弄熄了。我瞬间呆住,颜非也瞬间呆住。这……这条蛇成精了?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巨蛇扑了过来。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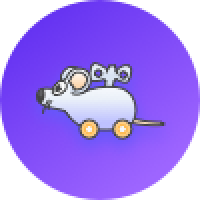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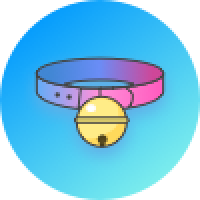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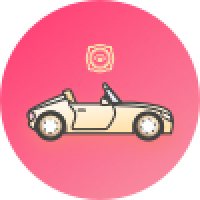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