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耳的警笛声响彻整座校园。
说实话,我已经不知是第几次用这样俗套的语句作为开场白了。我也想有所创新,但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语句能比这更好地表达此时的混乱。
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从窗户往外面望出去,满天满地都是残阳沥血的画面,那场景,像极了朝山村的那座老房子外面的天空。在那一刻我就突然有那么一瞬间的恍惚,几乎误以为时间倒流了。
我是被一队身着警服的人吵醒的。站在我面前的正是刘高和另一个叫不出名字的年轻刑警。
一如既往的询问,做笔录。等刘高他们总算忙完了,我就看见曾毅晖的脑袋在门边闪了一下,紧接着他整个人就跳了进来。
“怎么样?你还好吧?”看曾毅晖的表现以及出现时间应该是来探望我的,但奇怪的是,我从他的表情以及语气中没有发现一丝一毫属于探望的成分。好吗?当然很好,还没有死不是很好?我只狠狠地白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曾毅晖左右看了一阵,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到阳台那儿张望了一会儿,突然回头冲我灿烂一笑,说:“看来校医院的环境还是挺不错的嘛。”不错?我立刻就火了,心想环境不错你怎么不来躺躺试试?我心里火大,脸上的表情自然而然地就有些狰狞。
曾毅晖连瞥了我好几眼,他那愚钝的小脑瓜才总算开了点窍,立刻换上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对我表示慰问,说:“头还疼吗?我说你也真够倒霉的,收封信也能收成这样。”
我那刚刚熄灭了一点的火气立刻又窜起来老高,两只眼睛狠狠地瞪在曾毅晖身上,恨不得在他身上剥下来一层皮。真是交友不慎!我悲愤地想。后脑勺上被棍子敲中的地方一跳一跳地疼。
“看你现在这副样子就知道你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这回是赵子易。我扭头去看,立刻发现他穿着警服的样子居然有那么一点点锋芒毕露的感觉。
不知是我的眼神太过犀利,还是我的表情太过热烈,赵子易被我盯得冒出了一身冷汗,急忙把视线挪开,然后问:“你刚进4014教室时真的只看见那个上吊的学生?”我立刻点了点头。
当时教室空旷安静得就像坟墓一样,又是大白天,即使拉上了窗帘也不可能完全黑暗。别说是一个人,就算是一只小猫小狗之类的东西也很容易分辨出来。
见我如此肯定,赵子易也一时没有了话说,只静静地看着我,眉头紧锁。
其实当时的全过程是这样的。当时曾毅晖突然找我有事,连打了三个电话都是无人接听。最后,曾毅晖一个打到了苏琦那里。当时接电话的是苏琦的男朋友,由此还引发了一场信任危机。当然,这些就都是题外话了,直接略去。
从苏琦那里得知我已经出去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曾毅晖再次给我打了个电话,还是无人接听。这时候,曾毅晖才总算醒悟到我可能已经出事了,于是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学校。他一路不停地拨打我的电话,最终跟着铃声找到4014教室门口。
当时门已经从里面反锁了,被撞开之后,里面的场景立刻震撼住了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
据曾毅晖形容,当时他们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一双离地三尺多的脚,脚上穿着冒牌的耐克运动鞋。再往上看,就是一双下垂的苍白手掌。整具尸体正随着风不停微微晃荡,头则深深地埋在胸口的位置,一滴一滴的血顺着嘴角滴下来。
随着血液吐出来的还有一根舌头,耷拉着伸长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尸体的眼睛瞪得溜圆,眼珠里全是血丝,整张脸的五官就像信风带一般移动着扭曲了。
而我当时就正脸朝下趴在尸体正下方的地上,后脑勺上全是血,一动不动地就像个死人。
那种一生一死,一动一静的对比场面是无比惊心动魄的,据说刚分到赵子易队里的那几个小姑娘当时就吐了。
说实话,到此时我自己回想起来,也是满心后怕。我们都知道,后脑勺是人身体上最为脆弱的部位。这一棒砸下来可轻可重。如果砸得狠了,恐怕我立刻就得跟那上吊的男尸去做伴儿;即使砸得不狠,也难保我会不会留下点儿什么后遗症。反正我现在觉得自己还在喘气都算是上帝特别的恩赐。
而当时的情形确实诡异。所有门窗都从里面反锁了,只有一死一伤两个人。原本应该存在的第三个人就这样凭空消失了。整间教室立刻成为了一件巨大的密室。
“真正的密室是不存在的。”赵子易立刻说出了这句老掉牙的话,“我想我们一定遗漏了什么地方。”我笑了一下,等着他继续。
“我现在只对另外一件事感到非常疑惑。”赵子易突然把目光转向我。我立刻愣了一下,虽然明知道接下来的不会是什么好话,却还是条件反射地问:“什么?”
赵子易就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说:“我只是奇怪,为什么哪儿都有你?”我立刻愣在那儿,嘴边的笑容慢慢地就成了苦笑。我无奈地叹了口气,说:“说实话,我比你更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据说,这世上有这么一种人,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独体体质,这样的体质让他们可以看见很多人本来看不见的东西。也许是鬼魂,也许是幽灵……我突然打了个寒战。我猛地想起,我似乎也总是遇见些匪夷所思的事情,莫非跟这个有关?
但我这种总是遭遇奇特事件的状况却不是与生俱来的,至少在高中以前,我的生活都平静得如一潭死水。这些事情,应该是在上大学之后才频繁起来的吧。不知是学校的原因,还是异事谈协会的原因。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第二天是星期六,曾毅晖一大清早就开始狠砸我家大门。当时我正在做梦,迷迷糊糊地梦见隔壁好像有人不停地敲鼓,那声音还特别有节奏,“咚咚咚,咚咚咚……”敲得人心烦意乱。我突然一个激灵,从床上跳了起来,马上就听见曾毅晖在门外大叫:“阿舒,快开门,阿舒,快开门……”比闹钟还要管用。
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摇摇晃晃地过去给曾毅晖开门。刚打开一条小缝,就听见“嘭”的一声,曾毅晖已经自己把门推开,风风火火地冲进客厅,一屁股就坐在我家新买的沙发上。我看着沙发上那个被他压出的深坑,心疼地皱了皱眉。
“你快点收拾收拾吃点东西。”曾毅晖伸手指了一下他提上来的包子,说,“等会儿我们去见一个人。”我愣了一下,问:“谁?”
“是彭军的一个朋友,昨天听到消息之后就联系了我们。”曾毅晖拿起一个包子狠狠地咬了一口,里面的油汤立刻流出来,看得我心里直犯恶心。
彭军?彭军是谁?我愣了有好一会儿,然后猛地想了起来。就是那个上吊自杀的学生!
“谁说彭军是自杀的?现在恐怕只有你一个人会以为他是自杀的。”曾毅晖嘲笑了我一下,一边伸出他那只拿包子的手要来敲我的头。我急忙侧头,避过他那只油花花的爪子,不满地说:“你干什么?全是油!”
半个小时之后,我和曾毅晖到达“情与缘”咖啡屋,那个所谓的“彭军的一个朋友”早就已经到了,此时正静静等候在靠窗的位置。看见我们进来,她立刻起身,主动向我们做自我介绍说:“你们好,我叫苏宛,今年已经大三了。”
咖啡屋里的气味很奇特,不知是不是空调的原因,我一进来就感觉头很晕。我使劲晃了晃脑袋,直接问她:“你约我们来要说什么就直接说吧,我们听着。”
苏宛立刻叹了口气,说:“我还能说什么,还不是关于彭军的事。其实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我本来以为我都把它给忘了,可是当我昨天知道彭军出事时,我才终于明白,一切根本没有过去。”
我和曾毅晖都没有说话,只静静地看着她。这种时候,安静地倾听是最好的选择,或者说,我们对她即将要说的事情也的确很有兴趣。然而,直到五分钟过后,苏宛还是用勺子在咖啡杯里不停地搅动,估计是早已经神游物外。
我于是只能轻咳了一声,把苏宛的精神唤回来,然后问:“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公安局,也许对他们破案有所帮助。”苏宛苦笑着摇了摇头,说:“没用的,除了你们估计没有别的人回相信我的话。”“是吗?”我承认,我的兴趣已经完全被她勾了起来。
苏宛再次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们四个人从高中开始关系就一直很好。”我愣了一下:“你们四个?”“对。”苏宛点头,“我,彭军,代雅,还有王参。我们四个是好朋友。”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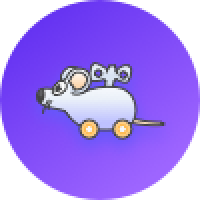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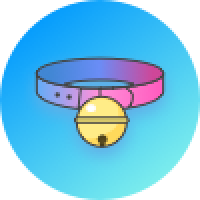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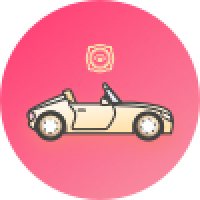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