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怎麽了?德聿察觉他的不对劲。太像了,这时的他像极了三年前一心 复仇的楚慕风,眼中因仇恨燃着旺盛的生机。
楚慕风凝视壁上那幅咏菊图,黑瞳灼灼的炽焰焚烧着决心是湘柔!她没死!?那 麽──这回她休想再次逃离他!
德聿,一待脱困,劳你即刻前往京城通知四叔为我筹办婚礼。
德聿挑高剑眉。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再认真不过。楚慕风沈徐的低音荡出简言易辞。
德聿睇了壁上的昼一眼。你就凭这幅画认新娘?可能吗?
一阵沈默。楚慕风眸光凝敛,专注地投注於相对默静的菊花图。
连我的话都不信?半晌,楚慕风的声音彷佛自幽谷低回成音。
你不是一时兴起吧?德聿摆明了撩拨。
楚慕风斜睇挚友一眼,十二分明白这家伙蓄意刁难。你玩够了吗?他们之间 从无须过多问句,若有一人决追根究柢定是图谋不良。
德聿掀唇一笑,矜贵的凤眼迸射出堪玩味的锐利。啧啧,认真了?此等反 机无多,怎可轻易罢休?她是她?吊诡的三字似是疑问实则肯定。
你话太多了。楚慕风淡冷的射去锋利一眼。
德聿挑眉,笑得愈发邪谨。意溢言表,心照不宣。
这家伙真的一脸欠扁!懒得理他。楚慕风自管凝悌咏菊图。
怎麽?不打算找人间明这画的作者?德聿悠哉的摇起玉扇,明知故间。
该出现的人自会现身。压根不瞧无事生非者一眼。
德聿扬起眉角暗叹。游戏玩不成了,无趣。
正沈默间,依凭二人武学的修为,闻知有人正往北方而来:来人步履飘浮,显 无内功基础,脚步细碎,应是一名女子。
二人对瞧一眼。楚慕风回首,又瞧了一眼壁上的咏菊图┅┅
如果叶湘柔的生命曾爱着一个人而绸缪浓冽,那麽,由於当初全然的交付,当 情爱走至尽头,即便的爱仍如出血般奔泄流出,而知觉却已封锁自闭。
撷自魂魄的热爱倾成了海洋,她立在岸边静望,再也不愿淌入那片出自她心魂 骨血的深郁汪洋。
她没有了记忆。
倘若日子仍要过下去,倘若地想存有一缕气息──她必须封锁记忆。
是在一瞬间明白的呵!那片自她身魂出走的汪洋,竟是窒死她的囚海。
切断了与那郁海的根连,剥离之际,唯一留存的,是瞬间悲沈的荒芜。
彻底根除一切的悲哀。
三年!好一段长长久久的日子。时间於它是没有意义的。
娘。稚嫩的童音轻唤。
她自团簇的菊花间仰起脸,淡淡的笑着迎向二岁约允 。
儿。她也轻唤稚儿,唯稚子让残生添上几笔喜乐。只是,笑容里却总揉 入了她亦不自觉的浓郁。小姨呢?小净离开渚水居已多时,回来还不及两 个月,允却日日同她腻在一块儿。
姨走了。允 儿抱着他的宝贝石板,一屁股盘坐在泥地上,就着灰板上刻画 儿。
走了?又走了?
嗯。 姨姨既已走了,允是来陪娘的。他喜欢娘身上的香香。
允 虽小,总明白娘是不快乐的。
儿,小姨说了上哪儿去吗?她搁下手上的花篮,蹲踞在稚儿面前。
没有!姨交代裙儿要守着娘,保护娘。三岁的允 活脱是个小鬼灵精。
湘柔眼眶微湿,想不到小儿子会说出这话。
儿┅┅不能守着娘一辈子的。她又如何忍心?教儿子一辈子随她耗在这 与世隔绝的渚水居?总有一天,允 得走出这座山坳,他得有自个儿的生活。
娘?娘又叹气了,允 也跟着拧起眉头。娘为何总不开心呢?
乖,替娘把花儿拿到膳房里,晚上娘给 儿做菊花豆腐盒吃。花搁到膳房後 就回房里洗把脸,手脚也一起洗乾净,然後乖乖上床睡个午觉。好吗? 揉平儿子 纠拧的眉心,隐化郁容,敛藏在深心底。
允点点头,拾起地上的花篮听话的跑开,他不曾拂逆过最亲爱的娘亲。
儿子走後,轻愁重回梢眼。又在园子分了为枝盛开的菊,悉心地摘去凌乱的菊 叶,收拾妥後便拿着整理好的菊花往远处小厅步去,打算为小厅妆点些新菊。
湘柔不曾预期厅里竟有个昂藏的男子,从容不迫地含笑等着她,新摘的菊枝散 落了一地。
你是谁?莫怪她吃惊,渚水居位於隐世山助,况且山助入口布有重重机关 ,外人绝不能轻易越雷池一步。
不是姑娘救了在?好一个美人!纤逸灵透,尤其经颦娥眉,更教人怜其楚 楚弱质。
湘柔不解,瞬目凝思。救了你?不,我不明白公子的意思。
不是她?德聿眸中迸出锐芒。
敢问姑娘,这处地方可是姑娘一人居住。兀自不动声色,想来眼前的美人 也不知何以凭空冒出一名闯入者。
我┅┅纵然眼前此人气度不凡,可他如何进得渚水居便是一个疑问,再者 水丫头曾道她师父的仇家甚多,若有找上门来的只会是一个目的──寻仇,报恩则 是想也别想的。
德聿察颜观色,为化去湘柔的戒心,他一派斯文雅尔的微笑,行止愈见优雅从 容。
整件事起因於在下误踏机关,昏迷之後不知为何人所救,姑娘显然非解救在 下之人,故而唐突一问。此番话四两拨千斤,将蹈入机关的动机技巧性略去。
原来如此。 湘柔毕竟涉世不深,岂能窥测德聿城府一角。想来是舍妹救了你。她与水净情同姊妹。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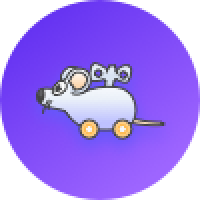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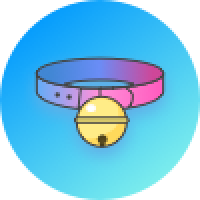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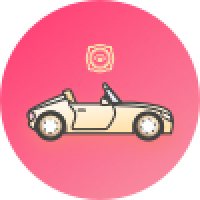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