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金花见姜庆东把自己扔给了余小华,他一副不关己事的样子,气就把不打一处来,像腾空而出的烟花,要在这里蔓延她美丽的毒气。
“冬哥,你说,你娶了这个女人,我们六个,你怎么处理?” 何金华声嘶力竭。以前,她不敢对姜庆东这么放肆,可今天,王八吃秤砣,她铁了心了,她一定要让姜庆东给她一个明确的答复。
怎么处理?姜庆东的头又一次大了,从复员回来,他也无数次在心里问过这个问题。这六个女人,都是自己年少惹下的,六个女人,自己都没有动过真感情,在今后的生活路上,自己一旦结了婚,把她们大发到哪里去呀?不能把她们纳为自己的小妾吧!就她们那点文化底子,再崇拜自己,也会是自己的绊脚石,就像华华说的,跌份儿,跌我姜庆东的脸!
不行!留下来,留来留去就是祸患,迟早一天会成仇人。
不留!她们是活生生的人,自己却不能像扔玩具似的给她扔喽!这可真是个难题!
姜庆东掏出一支烟,点起火来沉默起来,想着解决的办法。
男女吵架,男人保持沉默,就会叫自己的女人火上添油,何金花也不列外,她这几年,再怎么练淡定,在这个男人面前都无法让她那颗还很年轻的平静下来,她气的火冒三丈。但她知道,当男人沉默的时候,一定是厌弃,甚至厌倦了,姜庆东连喊叫或解释、辨白都不情愿了,看来他的心已经是死水了,哪里还有波澜和澎湃?
男人一向是在女人面前显示自己能力的,男人一向是讨好和巴结自己喜欢的女人的,男人一向是主动表白和陈述的。男人一旦沉默就意味着对女人的警觉、防备和厌弃。
姜庆东的不动声色,马上就激起女人何金花的愤怒,何金花早就领教到姜庆东这种损招,她想把所有的不满发向这个余小华,可在把矛头转向余小华的时候,她看到了余小华一脸的蔑视,叫她的心在瞬间就自惭形秽了起来。
女人杀人不需要动刀动枪,一个眼神,一句话,就能把自己的对手打下马去!
余小华扔给何金花一个蔑视的眼神,扔到何进华的眼睛里,就这么奏效,竟把想找事的何金花静悄悄的打败!
自己算姜庆东的什么?充其量就是他随便换下的一双鞋子,有了新鞋,当然要厌倦!要扔掉喽,自己和他要娶的女人比起来,就是天壤之别,人家是什么家庭背景,自己又是什么?不就是人们眼里的混混女?留在这里,还要在这里辩论什么?
自古男人三房四妾,冬哥是帮里大哥,有几个女人很正常,要娶这个女人,今后她就是大,自己傻啊!把老大得罪了!找屎吃啊!那几个妖精多精啊!马菊找她们商量,她们一个个装的义愤填庸的样子,说着冬哥要娶女人的各种坏话,可今天来搅事的,就自己和那个吃货徐静,剩下的的她们,到哪里去了呢?自己孤独无援,悲催!
自己要是再在这里胡搅蛮缠的话,冬哥要是发起威来,那大眼珠子一瞪,呵斥自己几声,自己以后如何在姊妹堆里混?
都是这马菊,说什么叫自己来搅黄冬哥的婚事。你看,人家两,手挽手,多亲,自己留下来,就是自取其辱!何金花想到此,三步并作两步,跑向了摩托车,戴起头盔,发动摩托,扬长而去。
可何金花却不甘心,又驱车回来了,冲着余小华大喊:喂!我们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你得意什么?
“嗨!嗨!她怎么跑了呢?”姜庆东在纳闷的时候,玉德饭庄对面的一家宾馆里的阳台上,四个漂亮入时的女人围着一架高倍望远镜在看玉德饭庄门口的动静。
“她敢给冬哥吹胡子瞪眼!牛!就是牛!”第四朵霸王花磕着瓜子,在望远镜里望了一会儿,对着剩下的三个在夸起她们的管理炮捻子徐静。
“叱!整个一个灭绝师太!牛什么牛?也就是整咱们的一个角色!你们看,有本事进去呀!像老五,人家就是进到酒店里堵他,你看,炮捻子却堵在饭庄门口,多掉价!还不是被他们羞辱而去?你看,那个姓余的,黏冬哥的那个骚劲儿吆!她妈的,我怎么没有防到冬哥回来这么一手!”一个个子超高,穿着一身清凉之极的吊带露肩装,露出圆润滑腻的珍珠肩,把她的衣架子身材衬托的玲珑浮凸,她懒洋洋的斜靠在望远镜边的一个角落,手里夹着一只快要抽完的烟,白皙如嫩藕似的胳膊随意垂着,那优雅的动作透着一种雍容华贵。在说完话的一刹那,她抬起胳膊,抽了一口烟,略仰起头来,眯起眼睛,把吞进去的烟,慢慢悠悠喷了出来,又慢慢吸了一口,随即又慢慢地喷出来,烟大了个漂亮的烟圈,仿佛给现场的一群女人炫耀她主人喷烟的技巧高超。
“就是,生米都已做成了熟饭,还能怎么地?搅什么搅啊!大家共侍一夫,这就是我们的宿命!”一个女人低着头,被几个女人半围着,透过不同身段的空隙,看不清她的长相,只觉得她整个人都笼罩在一片安静、纯明、柔美的气氛之中,声音里却透着一丝慵懒气息。
“老大,就是你的生性懦弱,才使冬哥纳了一个女人,再纳一个女人的,直到快要结婚,都没有把我们几个看在眼里!”在阳台不远处,一个女人端坐在一把椅子上,在翻一本杂志, 她 象一枝傲雪的寒梅,伫立在幽静的山谷中,恬静优雅的径自绽放,无论身周左右有多少人注视着她,她都象独自置身在空无一人的原野中一样,眼角眉梢,无不洋溢着自由浪漫的气息,还藏着深深的忧愁。
“唉!我怎么软弱了?我被他,我被他睡了的那一天,就很害怕他!害怕他打我,我劝他不要再害女孩子,他听了吗?谁叫你们一个个从小就长的是个尤物?你敢抵抗他?有种就去闹啊!以免被他送给兄弟娱乐,这样挺好!” 被围在中央的女人一声长叹。
“那我们就这样算了吗?我们才多大年龄啊!就被他打进了冷宫,他已三个月没去我那里,我孤枕难眠!”吊带装低头看着望远镜,那贪婪的模样,仿佛要从望远镜里把那个她朝思暮想的男人在望远镜里拉到身边。
“他三个月没去你那,他去哪里了,他从复员回来,我就没见着他!他说在你那里,都把我嫉妒死了!”很宁静的女人猛地抬起头,诧异的看着其他的女人,她想从她们的脸上扑捉到一点真实信息。
“我还以为他在亚芬那里,死亚芬五音不全,还玩音乐,玩了十几年音乐,不就是想拿点高雅把他的心靠拢?”嗑瓜子的一听有人提起敏感话题,她再也忍不住了,想姜庆东想的,她都恨不得找个机会,把几个抢她男人的女人统统毒死!可听她们一说,她知道,冬哥复员回来两年,没有去过这现场的四位女人家。
“哎呀!我们被他涮了!”四个女人琢磨了一会儿,忽然恍然大悟,大家面面相觑。
“哎呀呀!可恨之极,他把一身的独宠给了那个姓余的!太不公平!找个机会,要报仇!”
四个女人的誓言在玉德饭庄对面的宾馆回荡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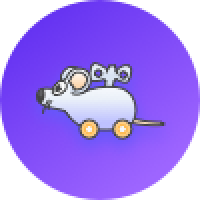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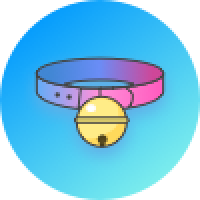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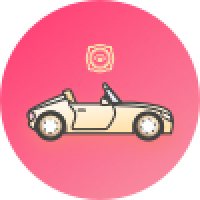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